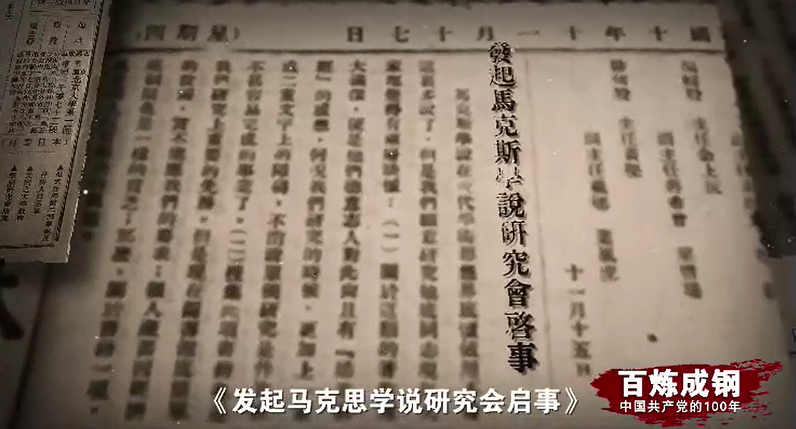前不久,臺兒莊大戰紀念館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戰場文物——一封家書。捐獻人馬風威講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78年前,馬風威的爺爺馬聚三在臺兒莊戰場上寫給母親一封家書,這是一首飽含深情的“獻給母親的詩”。

馬聚三,1907年出生在河南鞏義市米河鎮一個富裕家庭,哥哥叫馬光吾,兄弟倆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據老輩人講,馬聚三英俊威武,從小就練武,有一身好功夫,據說一拳能把碗口粗的樹打斷。后來,馬聚三不顧父母反對,毅然走出家門當兵去了。因為有文化,又練過武術,所以當兵不久,部隊就保送他上了軍校。
馬聚三當兵后,應該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曾回家探親一次。母親勸他說:“外邊太亂了,你父親年齡也大了,你還是回來繼承祖業吧。”可是馬聚三說:“現在國家山河破碎,日本人都打到家門口了,凡是有血性的人都不愿當亡國奴。更何況國家正是用人之際,我更不能茍且偷生。”他還勸父親把家里的地賣掉,否則會招來禍患。
馬聚三這次探家返回部隊后,就踏上了抗日戰場,一直沒有回家。從此杳無音信,是死是活,下落不明。
1996年,馬聚三老家村里的老中醫馬坦平翻蓋房子時,挖出一個封口的壇子。馬坦平想:這里面可能是金銀財寶,我們不能動。他連忙把壇子抱到了馬風威家里。因為在解放前,這塊地是馬風威祖上的牲口棚所在地。所以,馬坦平這算是物歸原主。
馬風威打開壇子,發現里面并不是什么金銀財寶,而是一封家書和一枚軍隊胸章。家書已經泛黃,殘缺不全,內容是“獻給母親的詩”:
母親,
我也曾想安逸地過我的一生,
我也曾想不踏進革命的危境。
可是,
在風凄露凝的清晨,
風清月白的黃昏,
我決不應忘了我所負的使命……
母親,
與其在鋼槍白刃下受辱偷生,
真不如在激烈戰爭中殺身成仁。
落葉聲聲,
打動了我的心靈,
我勞苦功高的母親……
這是一首表達作者對慈母思念之情的詩,也是一首向母親表白自己志向的詩。馬風威明白了,這是爺爺馬聚三的東西。可是誰埋在這里的呢?爺爺是戰死了?還是去了臺灣?
后來,村里的老人馬慧寅悄悄告訴馬風威:“我年輕時候和你大爺爺馬光吾是好朋友,他去世前告訴我,你爺爺是1938年在臺兒莊戰役中犧牲的。你爺爺犧牲后,馬光吾代替家人領取了遺物,不忍心讓你祖爺爺、祖奶奶和你奶奶傷心,就把馬聚三犧牲的事一直埋藏在心里。他把這些遺物裝在一個壇子里,封好后埋在了你家牲口棚的地下。”
馬風威為了證實爺爺是在臺兒莊戰役犧牲的,到檔案館、圖書館查了好多資料,但是都沒有查到。轉眼到了2016年4月8日,臺兒莊大戰勝利78周年紀念活動在臺兒莊舉辦,很多參戰將士的后代齊聚一堂。不死心的馬風威也趕來到處打聽,但是都沒有結果。正在他失望之時,遇到了前來參加活動的臺灣黃埔軍校同學后代聯誼會會長丘智賢先生。他就把爺爺的名字告訴了丘智賢,委托他在臺灣查查檔案,看能不能查到。丘智賢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
丘智賢回到臺灣后,查閱了好多檔案資料,終于在臺北國民革命忠烈祠找到了答案。丘智賢先生在J7-57號的牌位上面看到了馬聚三的名字,上面寫道:馬聚三烈士因作戰陣亡于民國27年(1938年)6月1日,1977年3月入祀。根據規定,將軍級別的犧牲者,有單人牌位供奉;校尉級的是百人合用的牌位;士官、士兵則以集體名冊藏置在箱子里,每箱有一萬個人的名單。馬風威的爺爺馬聚三是在100個人合用牌位上的,應該是校尉級軍官。2016年5月5日,丘智賢給馬風威發來“馬聚三烈士入祀資料”的郵件,被埋藏78年的秘密揭開了謎底。
筆者查閱了國民革命軍第27師參加抗戰的經歷,梳理出馬聚三參加抗戰和犧牲的過程:馬聚三加入的部隊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后改為第2集團軍)第27師。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馬聚三跟隨第27師在琉璃河、良鄉等地區抗擊日軍。1938年3月,27師奉命開往徐州東北的臺兒莊右翼布防,參加臺兒莊戰役,4月8日取得了震驚中外的臺兒莊大捷。5月,日軍集結重兵分六路迂回包圍徐州,企圖殲滅中國軍隊主力。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和第五戰區察覺了日軍的企圖,決定分五路突圍,實行戰略轉移。這時,27師受命駐守徐州西北九里山附近,與30師一起負責掩護友軍撤退。5月19日,敵步騎炮兵附戰車數十輛,在空軍配合下猛攻27師和30師陣地,兩師官兵與日軍浴血奮戰,掩護主力部隊轉移。據《第2集團軍參加魯南臺兒莊一帶作戰戰報》載:“官兵皆深明大義……雖孤軍重圍,仍極力苦撐,陣線屹然未動。”至下午5時,待徐州周圍的中國軍隊全部撤離,27師在師長黃樵松的率領下沖出日軍重圍,24日到達淮陽附近。“后沿途屢遭敵人追擊,損失奇重”。馬聚三應該在此時壯烈殉國,時年31歲。